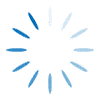叁年后。
王氏早已分家的叁房的长子近日娶亲,今日携同新妇过来国公府拜见。
郎才女貌的新人转过花壁,入目只见一座大厅,厅前仙鹤、孔雀种种珍禽,又有那琼花、昙花、佛桑花,四时不谢,应接不暇。
不多时数十个宫样妆束,执巾执扇的丫鬟捧拥着一位身量丰盈、已近不惑之年的美妇出来,这就是国公府老夫人张氏了。
叁人坐下说了会子话,新人便与张氏作辞,又转去了国公府中另一位主子院中。
此时正是六月尽,王之牧头带玉冠,穿斜领交裾长褐正立于院中撇骨池畔。
观棋上前禀报叁房族亲前来拜见,他不置可否,手上却一歪,将碟中鱼食尽数倾倒入池中,点头示意他把人请去中堂。
新人转过一重侧门,进的门来,见两下都是些瑶草琪花,苍松翠竹,此处的轩峻壮丽又与那老夫人的宝殿仙宫大不相同。
来此之前便有耳闻,自叁年前英国公的性情大变,将院中草木全换成了寺庙中所见的花草。今日青天白日来了他这处,果然恍如置身于古寺中。
入眼上面一间敞厅,不多久便有丫鬟忙捧上茶来,二人一面吃茶,一面打量,不多时只见一位目若鹰隼的威严男子从后头进来,二人忙起身作揖福身,又分主宾落座。
眼风扫到坐上之人,只见大名鼎鼎的英国公神情淡漠,不悲不喜,像位冷眼睥睨芸芸众生的神祗。
可他如今的名声却与这超脱出尘的相貌相去甚远,叁房二人联想到他如今的恶名更是有些瑟缩起来。
前段时日有言官翻出亲王一案,当堂指责英国公监斩亲王党羽时活杀生剁、斩首截肢眉头都不皱,在圣上面前口沫横飞了足足大半个时辰,参了他十条大罪,更是斥他为效似其父的阎罗酷吏。
新妇又不禁想起坊间传闻,去年初春时节圣上亲口为英国公赐婚,许的是当朝傅太傅长女傅幼玉。
可两家交换庚帖尚不过一月,圣上又传谕命英国公亲去督办太傅次子傅瑞书酒后强辱民女,女方以死明志一案。
据传底下人剖断官司时顾虑着二人的姻亲关系,便想着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没想被英国公亲口驳了,道是事关人命,岂可因私而废法。几场大刑下来,压着傅瑞书的手画了押,道是一命偿一命,判了身首异处之刑。
那傅太傅亲向圣上请罪,悔恨自己教子无方,秉着个弃卒保帅的打算,求了致仕。
圣上翌日便下旨准了太傅致仕返乡,却将死刑改为打五十大板后流放。如今傅瑞书人还在天牢里关着,不日变要被发配宁古塔。
因着这一风波,原本定在今年初春的婚期也因太傅夫人缠绵病榻,傅家主动开口延缓婚期而不疾而终。
当事人既然不急,便如此不声不响地拖延下去了。
连未过门的国公夫人都压不住这位煞神,英国公如今积威甚重,众人无不畏惧极甚。
叁人又疏离地说了会儿客套话,坐下二人如坐针毡,见王之牧面上已有送客之意,便忙不迭地告辞。
二人的骡车方拐了个弯,后头就有穿着气派的小厮手上拿了个扇套气喘吁吁地追来:“爷且慢,您落了件东西。”
也不是什么重要物什,如何就这般急吼吼追来,叁房二人狐疑地相视,还是命人停了车。
只见那小厮脸上透着股机灵劲儿,麻利地对着二人磕头。能在国公爷身边贴身伺候的人,二人不敢受他如此大礼,忙唤他起身。
这名为观棋的小厮将东西亲手交还给二人后,却自觉退了半步,弓腰垂首地客气问道:“国公爷本欲差小的送回您的府上,可如今见着了这上头绣的绿竹,倒让国公爷想起了老夫人格外钟爱去年做寿时送过的一盏绣屏,故特遣小的前来问上一句,敢问这上头的刺绣出自哪家绣坊?”
新妇隔着车壁同外头和声道:“这原是我亲自绣给夫君的小物,上不得大雅之堂,老夫人若是喜欢,改明儿我再奉上几件亲绣的物件儿。”
没想观棋倒是不依不挠:“敢问夫人这一手绣技师承何人?”
这话问从一名小厮嘴里问出来就有些觊越了,但观棋恍若不觉似的,仍是恭敬垂头,一副不问出个结果就誓不罢休的模样。
观棋是国公爷身边得脸的小厮,二人自是不敢轻视,车内之人思索了一番才缓缓道:“原是我闺中之时母亲为我请的绣娘,名气倒是不大,我看着不错,便学了一年的光景。国公爷若是看得起她,我免不了休书一封询她可有上京的意愿?”
观棋眯起眼,笑得狐狸似的,忙打恭作揖:“夫人这手艺,这满京里再找不出第二人,老夫人定会十分欢喜,小的也得见识见识。”
几人又客套了几句,张氏留了饭,这会儿已经催人来请,观棋这才辞了二人转回澹怀院。
*
叁房二人甫一离开,王之牧的脸色便急转直下。他紧缩眉头,令眉心那道纵纹越发深邃,独坐于堂中不发一言。
观棋不多时便回来复命,王之牧这副模样掉入他眼中,便轻易勾起他记忆中国公爷上一次露出如此隐而不发的模样时又有多少人遭了殃。
观棋顿时敛色屏气,将叁房二人所说一一和盘托出。
观棋所说的每一个字,听在王之牧耳中,都重若千钧。
他的胸中涌出一阵又一阵熟悉而又剧烈的灼痛,原本无甚表情的面上现出裂痕,整个人隐隐透不过气来。
不成,不能想起她。
可又忍不住升起渺茫的希望。
他方才惊鸿一瞥间,见那扇套上的修竹隐有似曾相识之感。叁房二人前脚刚踏出院子,他后脚便翻出了当年她绣在披风上的那丛绿竹。
王之牧当下便派了探子南下江南,这一打探便抽丝剥茧般地查到了广陵这两年新冒出的一座绣坊。
他又将叁房所送来的那绣娘亲手所绣的一张帕子摊开在桌上,又将其与披风上的并排作对比,顿时不免失望,二者并无丁点相似之处。
王之牧本是雀跃的心又沉了下去。
倒是他妄想了。
可直至半夜也仍是寝不安席,脑中竟被那刺绣填满,隐隐感觉不大对劲。
又过了十几日,探子从广陵寄来了密信。按信中所述,绣坊之主传闻是位叁十余岁的寡妇,丈夫叁年前病逝。探子去官府里核查了户籍记录,确是如此。
王之牧阅后默不作声,原是自己执念了,顿时颓然坐回椅上。
又过了数月,眼看到了十冬腊月,澹怀院的丫鬟们翻出箱底的厚衣裳,不免又找出一些旧日的绣品,因怕虫蛀,便趁着一日出太阳晒在了院子里。
北风寒朔,恰有一枚帕子落在了王之牧下朝回来的必经之路上。
王之牧远远瞥了眼,目光微怔,随即又步履如飞,上前捡起帕子,瞧了又瞧。
他蓦然想起这帕子还是那时她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绣的,找了她那兄长转卖。其实那会儿他已有意放她一马,见她兜中实在捉襟见肘,便命落子将先头那几件暗中高价买了下来。不过到后头时,她的绣品竟真是有市无价,再难求了。
当时他无心观赏,现如今再看这绣法,却与他披风上的那枚竹叶大有不同。
他心中再起疑窦。
王之牧掌管昭狱,故不费吹灰之力便寻了一位老成的绣娘过来鉴定。
绣娘看了半日,这才斩钉截铁断定道,那旧帕的技艺仍显青涩,到新帕时已是颇为成熟,虽稍有些不同,但定是出自同一人。
又过了十几日,王之牧派去广陵的探子再度送回一封密信,不过这一回,信中夹了一张女子的画像。
那摊开的画像上之人简直是对他莫大的讽刺。
他顿时将手边的金釉束口盏捏得碎裂,边缘锋利的碎茬将他手掌割得鲜血淋漓。他浑似不觉,哼出一道冷笑,如同寒刃划过心口,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眼睛再度扫过桌上并排摆放的刺绣,顿笑自己一叶障目,他虽不懂绣技,却对书画颇有心得。
这两丛修竹那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若不是他亲眼见过她是如何在绣架上穿针引线,若不是他这几日睁眼闭眼将这两块刺绣看得滚瓜烂熟,若不是……
他是庙堂尚修炼千年的人精,诸多蛛丝马迹很快让他联系起来,想到自己被蒙骗了叁年之久,却从未怀疑到她头上,顿时咬牙切齿。
不过,此次第一批派去的探子回报有高手守着院落,方才接近便被对方发现了,还重伤了一个。王之牧顿时不敢打草惊蛇,只让探子只看着她就好。
并且探子再报,有位名为姜涛的富商常去府上拜访,二人更有些不清不楚的名声。王之牧顿时怒气更盛,他本就奇怪她一弱女子如何一路南下,原竟是有了依靠。他冷笑,当年他的确怀疑过她假死,可去姜家祖宅打探的人来报,的确有位长相和姜涛相似之人在守坟。
可是不活捉到她真人,的确不敢盖棺定论。
是死是活,他定要亲眼见到。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