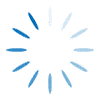她亦起身,随了众人缓步行至湖心,只见那处已陈设茵席,金罍玉觞与琳琅满目的茶果摆满了矮几。
又见不少云英未嫁的女郎们都戴上了素白的帷帽,姜婵拔下头上的一枚簪子偷偷塞进相熟的丫鬟手中,不多一会儿她便也将自己的脸掩在那长到颈部的薄绢之后。
她乖觉地寻了一处不打眼的树荫下坐好,心里巴巴望着宴席早日结束,好让她早点逃离这危机四伏之地。
王之牧前些日子要务缠身,实在腾不出手来。他来广陵不过一日,外务压身,再加上最要紧的是自个儿还未想好如何拷问她,倒是未曾贸然行动。
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这般畏手畏脚是什么时候了,哪怕斩皇亲国戚也是雷厉风行。自查到她还活着,恨不得亲手捏死她,心里头憋着这团火从京城里就烧起来了。
他实在是想不通,自己哪里对她不好了,非要弄个假死局来硬巴巴地诓骗自己。
又不禁烦躁起来,这一番大张声势、劳师动众将两艘船上的人都聚在一处,哪怕是个聋子哑巴也知道是他亲临了吧。
这可恶的小娘子为何还不爬着过来向他负荆请罪!
他方才在席上神思不属,等了大半日也不见人过来,倒是他先沉不住气,眈眈的打着曲水流觞的名义给她个门槛下。
拿了他的玉杯,总是要同他当头对面,把这过往因果都对得明白了。
可及至方才见到她了,心下又不知拿她如何是好,积攒了几月的满腔怒火隐约有烟消云散之意。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他想到此处,不由得板了脸。
姜婵只觉得周身那喧闹声一息间鸦雀无声,似是所有人忽地皆屏息静气似的。
她忽然心如擂鼓,后知后觉周身不论官妇还是奴仆,皆已要么搀着侍婢的手弯腰福身,要么直接伏地行礼。
她似慢了半拍,这才将挺得笔直的腰杆弯下去,低下头,没来由觉得心慌,双手扣紧草地,那惊魂未定之感在寥寥数个动作间神形毕现。
隔着数丛花木,从不远处飘来的嗓音却带着常年身居高位淬炼过的威严:“今日出来游玩,大家无需拘谨。”
哪怕他的嗓音又沉又缓,但如今他不论说什么都会不由自主显出不容置喙的强势。
姜婵叁年未听见这个声音了,也不知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那双唇一上一下,杀伐之气便已清清楚楚压在众人头上。
他如神邸般站着,平静的双眸穿过那若有似无的薄绢,沉沉的威压传达过来,女眷们煞于他的气魄,根本不敢抬头直视他的方向。
王之牧目光扫过,脸上笑意微收,神色不辨喜怒。他现今风头正劲,不论去哪处皆是前拥后簇。
姜婵一见这阵仗,虽也随着众人站立,却仍扒拉了几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帷帽,依旧是埋头缩颈躲在人后。
王之牧今日只穿了一件常服,大老远便瞧见他气质卓然地站在人群中央,带着股高门贵公子的慵懒之气。如若不是姜婵此时不敢正眼瞧他,只消看一眼便能轻易分辨出这身外袍便是她前些日子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衣裳之一。
只见皎如玉树的英国公手中招摇地擎了一支玉杯,众人眼色飞过,一时之间多少心思。
英国公虽未满叁旬,看着丰神雅淡,识量宽和,可无人敢这般小瞧于他,他这几月来亲口下令虐杀斩首高官如切瓜剁菜,圣上不以为忤,甚至还嘉奖了他。
姜婵只敢快速抬头打探,却瞧见了那抹玉润的颜色,一颗心顿时跳如擂鼓,冷汗爬上脊背。她力持镇定,下意识便将手掩在衣袖中,顺带也将那枚玉杯遮住。
她面色虽看着还算平静,可实则如坐针毡,只觉得这偌大的岛屿再无她的立锥之地。一旁站立的丫鬟见方才还是落落大方的柳娘子,已缩手缩脚,恨不得把自己缩小成地上石子。
王之牧毕竟风姿出众,哪怕气场骇人,春宴中仍不乏有那举止大胆的妙龄女郎,主动迎凑上去。
该来的人没引过来,不该来的却蜂拥而上,他压下心底的不耐,因他城府渐深,眉峰一耸便是扑面而来的杀气凛冽,近身的人只觉得他眼神凉沁沁、阴森森,那刚还凑过去的人顿时不敢作声,一下子又鸟兽散开。
这一阵一阵的又闹又静,令得岿然不动的姜婵也忍不住好奇抬头,四目交汇间,他的目光不避不闪,如炬的眼似有情绪从他的眼眶中呼之欲出,风平浪静之下他仍在极力压抑。
姜婵的心倏然抽紧,身体仿佛被野兽的利爪紧紧踩住,动弹不得。
他……他知道自己在这里!
她遍身的寒毛都竖立起来,明明是春日醺风,却只觉一瞬成了数九寒天的朔风顺着襟口、袖口、裙脚倒灌了进来,侵肌刺骨。一旁的小丫鬟不解地偷偷推她:“柳娘子,怎生抖得这般厉害?莫不是病了?”
这一声不啻于醍醐灌顶,姜婵脑中滚过万千个装病的法子,可如今他那势在必得的姿态,哪怕是自己现下立刻晕倒,怕也是会被他一眼看穿。
她手足微颤,思来想去不知如何逃脱。
王之牧眼中带着得色,明明白白透过那纱幕看到了她的怯,他漫不经心地将双手端于袖中,不慌不忙地走来,凝向她的眼神却是锐利逼人,仿佛世间尽在五指山下,犹如蛰伏已久的饥兽正对着瑟瑟发抖的猎物伺机而动。
恰在此时,身旁传来一声惊呼:“夫人,您怎么了?要不要紧!”
原是一位官妇本就身子不爽利,今日吹了半天的风,旧疾犯了。王之牧那慑人的威势压过来,姜婵还没倒下,倒是把她一个不相关的人吓晕了。
姜婵立刻见机而行,忙上前对着那家人敛衽而拜,道是自己懂些医术,不如将人抬至画舫,自己先来照料她,待上岸再找大夫细细瞧过。
姜婵兵行险着,但幸好今日并无医女同行,众人也只好先同意了她的法子。
王之牧总不好当着众人的面坦诚自己今日是来捉拿逃跑的外室,也不好光明正大阻止救人,只能眼神越来越冷,凌厉的眼神扫过她的背影,像一把刀子。
她头也不回,就像雀鸟逃出樊笼。
王之牧眼风一扫,她刚才立身的树下,躺着一枚孤零零的玉杯。
人既已跑了,王之牧意兴阑珊地摆手。他虽面上不显,但心中不喜,总有些不露声色的威严在,吓得宴会上众人再不敢嬉笑。
“你将我变成这样,却一而再再而叁地弃我而去,好……好……”
几乎是画舫靠岸那一刹,船夫口中的号子余音还未散,船还未停稳,姜婵已拔腿就走,弃船奔逃。
她过了叁年自由自在的舒坦日子,决计不要再回到那关在牢笼里的日子,不清不楚的为人外室,镇日围着王之牧这个能对她生杀予夺的主子。
哪怕连多呼吸一口,都像是自己从那高高在上之人那里费尽心机乞求而来的。她就如同他手中的提线木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依照他的喜好。
她自觉跟王之牧不过是露水情缘一场,各取所需,互不相欠。
一想到王之牧,便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惧怕,可隐隐又有种破罐破摔的期望。
之前忧心他循着蛛丝马迹发现自己还活着,如今破罐子破摔,反正她这些日子先去外地躲着,捱到他回京不就好了,她才不信这么个贵胄会为了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而兴师动众。
姜婵回去便迅速收拾包袱,正磨了墨,摊开宣纸,才刚写了个开头,未来得及交代清楚前因后果,太仆寺卿夫人的丫鬟便已在门口候着,道是夫人有事请她上门。
姜婵不敢不从,遂只好将写了一半的书信放下,略微整理了几下衣衫,抓了张一千两的银票塞在袖里,便随着传命的丫鬟跟着去了。
路上她塞给那随车的小丫鬟一个银锞子,欲要打听所为何事。那丫鬟却借故推脱,道是夫人在家恭候着,不是什么大事,柳娘子无需忧心。
可哪有这样凑巧,她也是上了马车不久后才后知后觉到不对劲之处,再加上方才丫鬟那恭敬客气的态度,虽说交浅言不深,一句话的就能到手的银子哪有不收的,反常必有鬼。
带着忐忑的心思她进了太仆寺卿府,看到座上的李氏时却怎生看怎生觉得她脸上的笑容太过灿烂。
姜婵只作不知,心中虽有些打退堂鼓,但来都来了,总不能转头就跑。
李氏热络地拍着她的手,道之前那贵人只准备在广陵待一两月,如今又多了些杂事,怕是要待到年尾,所以连着秋冬装的衣裳也要一块做了。这回还是请她亲自来绣,她前几日交上去的东西那贵人很喜欢。
以往李氏顺手为她推荐客户,姜婵都是喜不自胜连声感谢,可如今就跟见了鬼一样。
她斟酌语句,蹙着眉道,不巧绣坊近日接了个大单,她势单力薄,怕耽搁贵人的时间,只好拒了。
她给的理由合情合理,倒是让李氏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李氏只好话锋一转,顺口提了一句,近日那位大人有事,临时出了城,怕是近日都不会回来,所以无需着急,反正离冬日还尚远,先接下,赶得及做就成。
姜婵下意识又要推拒,却被李氏握紧了手,眼神里似是带了警示,若是绣坊丢了这笔生意,日后再上这样的好事,只怕也无人再敢上门了。
李氏不愧是执掌中馈,掌管府里上下上百号人口的主母,一句话按住了姜婵的死穴,她听音辨意,再不敢婉言推拒了。
李氏遂笑眯眯地拍拍姜婵的手背,姜婵没想自己弄巧成拙,一向妙语连珠的她一时僵在那里,挤出个干巴巴的笑来。恩典的名头砸下来,她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进退两难。对方有备而来,自己好似赴了鸿门宴一般。
这是霸王硬上弓,先把什么都定死了才来下通牒呢这是。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