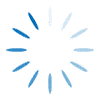姜婵怏怏出门时暮色已沉沉,广陵府无宵禁,大晚上的她连能去哪里都还没想清楚,但心神格外不宁,赶着城门还未关,去马车行好说歹说多使了银子雇了个车把式,预备趁着月色先出城躲一躲。
但马车驶到了城门口却发现一排手持红缨枪的官兵列队站着,那肃杀之气看的她直打怵,旁人道是近日要捉拿犯官党羽,出城进城之人不论去何处都要先行登记。
要登记她还逃个鬼。
她一连跑了四个城门皆是如此,遂挫败地结了车夫钱,无力无气地嘱咐他将她送回燕子巷即可。返家后看到案上没写完的信,烦躁的把信撕了,揉成一团。
这时搬了个小杌子在外间做了大半天针线的小丫鬟云肩瞧见了她这暴躁的模样,一瘸一拐地站起身望了望,见她对着虚空深吸了几口气,似乎平息了情绪,这才上来禀报:“娘子可要摆饭,盘金姐姐这两日歇在绣坊里,暂时不回来了,让娘子无须担心。”
姜婵摆摆手,表示知道了,如今却并无胃口。
她一一给写着“故显考余老之灵”、’“故显妣余氏之灵”、“故女弟子姜氏”的牌位上了香,只觉得今夜的蜡火狂跳,恰似她此时的心跳。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但奈何今日跑了一整天,浑身黏糊糊乱糟糟。她吩咐婆子抬了香汤,泡了小半个时辰才出来。对镜梳妆时,打开一盏神仙膏,那扑鼻而来的清香令她混沌的脑中一醒,顿时计上心来……
第二日一早,太仆寺卿府上就收到了姜婵退回去的布匹同定金,还歉意的附上了叁成的违约金。
姜婵惬意地躺在床上睡到将尽午时,正想着怎生打发今日的时间,门外却听见闹哄哄的声音。
差不多也是时候该到了。
她却不准备起身,而是吩咐云肩去前头招待,自个儿则披上了外裳斜靠床头,瞬间化身病西施模样。
不多一会儿一阵脚步声到了卧室门外,眼见叁两个人影要越过床前屏风进来,姜婵忙哆嗦着声音,犹如惊弓之鸟般对着外间几人扬声道:“别进来!许是会传染。”
外头那几人果然瞬间止住了脚步。
姜婵遂又啜啜泣泣地拿了帕子抹眼睛,对着外头的人影哭噎:“烦请转告太仆寺卿夫人,这病来得急,妾身深恐有辱使命,耽误了夫人的功夫。幸而还未动工,只好战战兢兢将您送来的定金退回。妾身今早已差人去问过其它几家绣坊,只好劳驾它们了。”
“那病果真会传染?”
那声音,竟然是太仆寺卿夫人。能劳累李氏亲临她这小宅,这就更坐实了背后有古怪。
她铤而走险装病也是被逼的,照李氏昨日话中的意思,王之牧人如今不在广陵城中,想来只要熬走了他,她兴许就自由了。
思及此,姜婵遂又用那叁寸之舌编出一段故事,道是怕这病传染给别人,自己打算这两日出城寻个偏远的庄子养病,什么人都见不得了。
谁料那李氏人虽退到了外间,但却没那么好打发:“这传染疫症可是大事,我刚才听闻此事便带了府上的大夫过来,这人乃是宫里头退出来的太医,医术高明,亦曾参与十几年前京中大疫的诊治。柳娘子,若你确实身染疫病,怕是要劳动官服来人将你收至寺院的收容所里了。”
言罢,李氏便差丫鬟去把外头候着的大夫叫进来。
这还给不给人留活路!丝毫不给她喘息之机。
姜婵只好认命的穿戴整齐坐在床沿,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用一块白布遮掩了口鼻走了进来。
李氏也戴上了蒙口鼻的绢布,远远越过屏风看了一眼,见她脸上、手上露出的肌肤确实遍布红点,心下却仍有疑窦。
已至花甲的大夫皱着眉,把了半盏茶的脉,左摇摇头,右摇摇头,看得屏风内外众人皆是心里没底。半晌,他才收手道:“娘子定是冬日受了风寒,风邪和寒邪淤积在体内。近日春天阳气升发,正气驱逐邪气,遂引发丘疹。”
外头的李氏比姜婵还急切地扬声问道:“可是疫病?”
“不过花粉症而已。”
姜婵闻言顿时脸红,这算是当面被揭穿了。她下意识抬眼看了看外头的李氏,却对上了她蕴含怒气的眼。
那老大夫却不见李氏和姜婵二人的眉眼官司,继续摇头晃脑道:“当用温药和之,把体内的风邪和寒气散出来就无事了。”
姜婵亡羊补牢般地忙解释,原是自己见识浅薄,看到长红点就差点以为是疫病。又干巴巴讪笑了两声。
“……既然只是花粉症,想来不过几日便能痊愈。先前的活计幸得那位大人青眼……对柳娘子你知根知底,你亲自来做我才放心……”
李氏将茶盏递给一旁的丫鬟,再用帕子摁了摁嘴角,对着仍坐在被中的姜婵一通训话,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令姜婵深感惭愧。她活了两世,都鲜有这样损人不带脏字的口才,不愧是浸淫已久的官夫人。
姜婵如今已经是李氏说什么话都得接着,勉强做出副铭感五内的模样。
李氏施施然离去之时,姜婵再不敢托大,外头搭了件披风执意要送李氏到门口。
她恭敬送李氏上了马车,却总觉得有一道不善的眼神正落在自己身上,她顺着望过去,目光却落在一名身着褐色澜衫的少年上,随即愣了下。那桀骜的少年正抬着眼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她,她瞪回去,他却半点退让的意思都没有。
她突然脑中闪过一段记忆,蓦地想起这人!这可不就是那个讨厌的、总跟她过不去的总角小儿。叁年不见,他倒是变化颇大,差点没认出来。
可他为什么会陪同李氏来此?
姜婵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当即消失无踪。好不容易送走了李氏,她只觉得头大如斗。
她唤人去外头叫了个说书的小童,两片月牙形的鸳鸯板儿铮铮作响,上下两张嘴皮侃侃而谈,那小郎口吐明快的唱词,辅以惟妙惟肖的表演,将广陵城近来新鲜事,尤其是新来的英国公事迹,又说又唱讲得一清二楚。
姜婵的心越听越凉。
是夜,姜婵于梦中惊悸。
前头一片漆黑,阴风窜窜,青面獠牙的恶鬼慢条斯理地剥开了脸上的皴皮,露出王之牧辨不出神情的脸。
他绿幽幽的眼睛正直勾勾盯着她,一只血淋淋的利爪踩在猎物的背上,咆哮已经在喉间蓄势待发,獠牙龇起,凶相毕露,对着猎物的喉间……
她尖叫着惊醒,抱着被子在床上静坐了半晌,这才慌不迭地点烛、趿鞋,推开书架后一块不起眼的挡板,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盒。不多一会儿,这些年辛苦积攒的家当都被一一摊开在床上。
除了房契、地契以及带有国公府印记的那些不好变卖的珠饰,当年王之牧赏下来的东西,她零零碎碎地攒了五千两银子。
那时她嫌弃王之牧玩什么低调的奢华,赏赐之物大都华而不实,不好变卖,那么一大堆里捡出能卖的也不过堪堪凑了五千两。此刻还钱时方才觉得幸好幸好,否则他随便丢下的一根玉簪怕都是价值连城。
如今绣坊虽不是日进斗金,但赚得也不少,此刻却从哪里能硬生生抽出五千两啊……再说恰好碰上姜涛也不在,真是噩运排着队给她找绊子。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既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心疼!
回想起自己叁年前尚还为这变相的“卖尻钱”而悲从中来,如今却……
罢了,破财消灾,就当她主动睡了那男人一年吧。想来古往今来也找不到比她更窝囊憋屈的外室了,赔人又赔银子,她磨牙了一阵,许是失了银子的怨气盖过了害怕,她竟真的安稳入睡了。
翌日一早起来,姜婵发现身上的红疹几乎全部退去,可更大的麻烦还在等着她,恍惚间有山雨欲来之感。
既然躲不掉,她决定见招拆招。
她一早将昨晚翻出的珠宝地契送至当铺,回来时,身上便多了一张银票。
她不是媚想过抛下一切,趁夜色坐快舟逃跑,可她如今哪里还能抛下绣坊的女孩子们。罢了,自己与王之牧那段孽缘牵涉的不过就是财。大不了面对他时,主动归还钱财,再他不论有什么火气,自己都生生受着。
忍,一定要忍。
就当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就当是为了绣坊那几百名命途多舛的女子们,就当是为了断干净以后好好生活……
她坐于镜台前,细细在脸上、脖间以及手腕上涂抹一种黄粉。这种“黄妆”原本盛行于北方游牧民族,所用之粉是将一种药用植物的茎碾成粉末,原本是用以抵御寒风沙砾的侵袭,开春后才洗去,皮肤会显得细白柔嫩,如今她要用这粉来“易容”。
忙活了一大早,她再细细端详了半日,确定这一番巧手装扮后,面上添了风霜,亦和柳佩玉的真实年龄接近不少,这才稍稍松开紧皱的眉头。
没了好颜色,自然也会遭到厌弃。
她绞着手指白白干熬了一整日,直到外头响起打更声也无人上门。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她带着满脑疑虑,压下前路未明的惶惑无助,却一夜辗转难眠。
昨日脑中那根弦绷紧了一整日,今日她斜倚廊前直到暮色渐浓,见始终无人到来,这才安心,正准备唤人抬水时,大门外却突然传来“笃笃”的叩门声。
“笃笃。”那催命声又起,似是叩门之人愈发不耐烦起来。
“叩门者是谁?稍安勿躁。”外头的婆子想是终于举烛启扉,来得频甚的叩声终于止住。
姜婵心道,来了。
直到这一刻,她才有那在脖子上悬了两日之久的刀终于落下的轻松感。
她有条不紊地收拾衣裙,临出门了下意识摸了摸头上那根金簪,想了想,还是将它放回妆奁中。
这回应当用不上它吧。她如今过得幸福,很是惜命。
云肩边替她掌灯边嘀咕,谁家大半夜要做衣裳啊,又见姜婵脸色难看,不敢多说。
姜婵阻止了云肩一同上车,捏了捏她的手道:“若是明日日轮亭午我还未回来,你就拿着这封信去找姜大郎罢。”
姜涛去了外地进货,算着日子,这两日也该回来了。
“娘子,包袱?”
姜婵这才如梦初醒般接过出门常带的包袱,里头不过放了些针线尺子刀剪等常用物件,挎在胳膊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宛若赴死一般踏出房门,由来人领着,倒不如说是押着,走向门外候着的马车。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