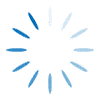男人的头颅俯下来,贴在她耳侧,索性单刀直入地问了一遍:“戏耍本大人叁年,有趣吗?”
姜婵眼角一抖,事已至此,她扔在垂死挣扎,她捻起假装的笑脸,正欲开口,他的手便已适时地抵在她的唇珠上:“你想好了再说。”
面前这位小娘子满嘴谎言,他执掌昭狱,听堂下犯人掰扯瞎造不知凡几,往往对方还未开口,他只从对方脸上细微表情一眼便知。
姜婵本能搜肠刮肚地要吐出那蛊惑人心的话语,且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真挚得不似作伪。她眼瞳乱逛,抬头间却正对上他挟冰含雪的眸子和不怒自威的脸孔,心里发憷,却强自正色。原来他一直这样面容肃穆,如同审犯人般的看着她的吗?
王之牧收起脸上的嘲讽笑意,释放出一点儿上位者的威压,厉声道:“同我说实话。”
她的舌尖似荷叶下滑过的一尾游鱼,不经意间舔过他的指腹,令他眼神更加深邃。
她张口,将那久经酝酿的谎言娓娓道出:“实则是当年火灾被歹人迷晕掳走,后因怕大人怪罪,故无言再见大人……”
话未竟便被他打断,他沉声再强调了一遍:“说实话”。
他冷静的外表下压抑着磅礴的郁气,蓄势而待发,她被质问得一僵。
罢了,她自己都不信的胡诌之语,为何会妄想能骗过他、
她怔住了一瞬,嘴唇颤了颤。从她遇见他那一刻起,她便被折了翅膀。累年积攒的不忿、委屈、失望糅杂于一处,被他的这把高高在上的质问点燃,引出绵延不绝的怒火。
他与她,从来不是对等的地位:“因为我被迫委身于你,为奴为婢,我只想摆脱奴籍,像个人一样过平淡日子。”
话至最后,她的声音在无法克制地轻轻颤抖。
顿时,他只觉心如被钝刃狠捅数下,她原是这般厌恶待在他身边。却因从未见过她这般锋芒毕露的样子,反生出一股扭曲的快意,他觉她如今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新鲜有趣,拊掌以示嘉奖:“倒是胆子见长,士别叁年当刮目相待啊。”
他在那个叁年上加重了语气。
姜婵无视他讥讽的目光,复又跪地:“妾身蒲柳之姿,不敢妄想陪伴大人身侧,愿归还所得钱财五千两,望大人看在妾身这些年悉心服侍的份上,放妾身一条生路吧。”
她心里不住打鼓,额头抵在冰凉的玉砖上不敢抬起。她一时孤勇,却也生怕触怒了他,自己连同哥哥一家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话音未落,王之牧便躬身向前,姜婵只觉得头皮被慢慢攥紧,勒得她生疼,被迫仰起头直视,她不敢试图挣脱,因她整个人都被他狂热的目光镇压得颤抖不已,根本无力再挣动一下。
王之牧难得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娘子释放出全身的威势,摄人的气场有如实质大网将怀中瑟瑟发抖的妇人层层包裹。
他如今玩弄人心的本事臻于化境,想要震慑她,易如反掌。
“我未松口,你便是求死也不能。”他用温热的指腹揩了揩她的侧颊,却没有变化。
王之牧那双眼诡谲难懂,敷着再枯黄的脂粉,穿着再老态的衣裙,她也依旧有那个本事让他心猿意马。
他扯着她的臂来到案边,她浓密的长睫惊慌地乱颤,他手上一抖,却将一盏温茶从她发顶兜头倒下,顿时茶叶、汤水狼狈的流了她一头。
枯黄粉末下,抹出一片犹如剥壳鸡蛋般的素肌
她惊叫一声,王之牧却已扬声命人将她带下去洗漱,重音却放在“将她的脸洗干净了。”
她挣扎得厉害,不让人近身,一旁众下人顿时不知如何动作,王之牧顿时暴怒:“都出去。”
他怒了,忠诚的宠物再顽皮,主人召唤时,刻不容缓投怀送抱才是令他满意的回应。
她怎敢!怎敢!
戏弄了他叁年,怎么敢!
观棋领着几人忙不迭躲避,阖上房门。
王之牧不管她的大挣大扭,双臂扣紧了他,粗暴却娴熟地将她的头按进水盆里,胡乱抓起丝帕抹过她的脸,二人衣裳顷刻湿了大片。
他日常惯例下令施以水刑时,被束住手脚的犯人的头被强按在水里,行将溺毙之时再被拉出吸口续命的气,如此反复几次,哪怕是铮铮铁骨的壮汉都受不住。
擦脸的丝巾颇用了些力,她有些吃痛,可却也比不上那一次又一次接近窒息的淹没感。
“不……”她挣扎得越厉害,他的力道就越狠。
在这致命时刻,她脑中却只有说书小童嘴里描摹的他——英国公城府在胸,连弑多员高官,行事暴戾而乖张,处事果决而狠辣——如今他已不再是她记忆中的那个男人。
她似被莽兽踩住了后颈的幼猫,本能的动弹都忘得一干二净。
折腾到最后,她终于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呛得肺都要咳出血,抖如筛糠,令他大发慈悲,饶过了她。此时她面上已是裸容,他掐着她的两颊,莹白面色、淡淡唇色皆因失了血色越发脆弱,却偏偏头发乌黑黏在脸上,衬得那张湿漉漉的脸越发无辜。
他心头猛地一漾。
比之姜婵的湿身狼狈,镜中的王之牧除了面色狰狞了些,依旧是衣冠楚楚,仪态翩翩。
他畅快地发现自己失控了,既然那些时日的温柔换不来她半分真心,暴力些又何妨?
他一反刚才的暴怒,声线多了些柔情:“婵娘,你如此不乖,想是忘了我的手段。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再回答我一次。”
她还未张口,他便控制不住地偏过脸,将吻落在她尚在淌水的漆黑鬓发上,将那朵微透的耳垂衔在口中,眼神却骤然转厉,“你若坦诚些,好言求我,今日我便放过你,就当一切从未发生过。”
姜婵打了个哆嗦,浑身汗毛耸立,下意识轻轻推搡了他。
不是不动心的。
当年她无论做了什么逾矩的错事,只要将乖巧的将头颅伏在他的膝上,让他手掌抚摸她的发顶,求得他的原谅,就会当做无事发生。
旋即又忙将这掩耳盗铃的念头扼住。
可她不想,再怎么害怕也不想,那是华丽的鸟笼,却让她窒息。
身后之人永远高高在上,随便施舍点什么给她便要她扯嘴假笑来跪求,她若不接着就是不识抬举。
她藏着一肚子无伤大雅的小心机,他心知肚明,逗乐一样养着她。他喜欢看她贪他钱帛,他图她擅弄风月。
她如今名为柳佩玉,并未卖身给他。哥哥前年托人去探查过,姜婵因身死已销户,世间再无姜婵其人。而柳佩玉孤家寡人,并无亲眷,她咬死了自己就是柳佩玉,还能有谁反驳她。
方桥村的寡妇姜婵已死在那场大火中,芳魂难觅。
她若仍是方桥村那受人欺凌的寡妇姜婵便也无可奈何,可如今她事业小成,家人安康,再不愿蹚他那处浑水,亦不愿回再做他掌中那金丝雀,日日身着华服等他来幸。
浮生不过短短几十年,与其苟且活着,不如硬气,大不了撕破了脸,仰人鼻息的日子她不愿再过一天。
她渐渐坚定的目光,已道尽了一切。一直密切关注她脸上动静的王之牧忽然不愿听她巧舌如簧。
他发着狠,比她还率先张口:“你愿与不愿,都是我的逃奴?”
他反剪她双手在身后,“痛……”
她此时任何的呼痛却换不来他的半分心疼,他双臂遒劲,她便一丝一毫也动弹不得。
手上一扯,衣襟大开,伴随她一声尖叫,顿时一双凝乳似水滴垂荡,他拇指捏弄那坟起的透粉尖端,捻着她一捏便硬挺的乳首,蛊惑地说:“这乳还是那般的浪。”
她此刻却不敢再出声,竭力扭开头,却被他将她面庞拗向镜子,看着那骨节分明的大手渐渐下移,在亵裤底下拱出明显的轮廓,不多时,传来布帛撕裂的声音,她不由打了个哆嗦。
她一只膝弯被不可抗衡的强力打开,被迫挂于他的臂肘,门户大开,那脐下唇儿便毫无遮掩的从亵裤一线天中露出,只见他不打一声招呼便伸出两指拨开花唇,呼吸却错乱了一息:“这尻还是同样的淫。”
久未得人造访的穴内软得一塌糊涂,他的两指只是浅浅拨弄,便引起一小阵痉挛。
“呜……不……”
她被他这简单动作拨弄得心弦又乱。
她的挣扎在他怀中不过是小打小闹,那只方浅捣过她穴的指捅入她咬得发白的唇瓣间,她尝到了自己的味道:“这嘴却还是一样的硬“,他顿了一顿,似是恨得牙痒痒,补了一句,”满嘴谎话。”
“婵娘可知我素来是如何惩罚逃奴的吗?”他张开一上一下两颗尖尖的犬齿,把颈边细嫩皮肉叼住,扯成薄且透的一层膜,脑中现出梦中那只咬着猎物脖子的凶兽,她似被咬住了命脉,不敢再动。
他压下想要将其蹂躏的欲望,拇指食指捏住那粒鲜嫩的淫珠,颤颤巍巍探头,却被带了薄茧的指揉弄拉扯,伴随他轻描淡写道出那血腥的手段,逼出她抽抽噎噎的呼救,转而激荡为撩人压抑的哭泣。
她双臂被困,无招架之力,恍惚间似是将她的头又暴力浸入水中,溺毙之感袭来。
她蹬腿扭身要躲开,却被他反压于镜前,穴瓣间那粒可怜珠蕊却挣脱不了粗指的磨砺,实在无辜。
他好似用虎爪在蹂躏一只幼兽,欺凌人般的扭曲快感点燃了他沉寂多年的情欲,令他无比亢奋。
她侧脸紧贴镜面,胸前的丰盈嫩软被挤压得变了形,越发沟壑深深,尖端两朵梅瓣磨砺在冰冷的镜面上,瞬间硬挺,竟还发出了艰涩的摩擦声响。
“啊……嗯……疼……”
他叁年来都未硬得这样厉害。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