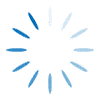我冷冷的看着他,我觉得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冷过,又冷又硬。
我伸出手,狠狠的擦了擦嘴唇,我怕擦不干净,又用力抹了抹,抹得我的嘴唇红得似火,火辣辣的疼,我才缓缓的放下手来。
我想起我曾经跟他说过的话。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愈合的,就是别人心上的伤口。
因为痛的永远不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所有的悲恸,所以他就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伤口,都能够愈合。
有的伤口是永远也愈合不了的。
就像项远永远也活不过来一样。
就像是我当初抱着他的骨灰,送给项艺涵时,心里裂开的那道口子一样,永远也愈合不了。
我冷冷的笑了一声,目光冷静的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一样,看着他。
我越是这样沉默,他身上的气势就越是压迫人,峻厉的眉眼像是染着寒霜,胸口的起伏越发剧烈起来。
他像是一点也不想看到这样表情的我,再一次朝着我凶狠的压了过来。
我们就在医院后门的角落里,我的后背膈应着水泥围墙,疼痛,却又清醒。
他像是一头侵略性极强的豹子,对着我攻城略地,炽热的情绪恨不得就这样全部滚烫进我的心里。
而整个过程,我不反抗,也不迎合。
从医院回到他的住所,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回到他的住所以后,我直接回了卧室,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景物。
裘钧扬在厨房煮东西。
自知道我怀孕以后,裘钧扬还没有让佣人给我做过饭,这两天都是亲力亲为。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亲自做饭给我吃的时候,朝着我道:“我已经十多年没做过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我也记得他怕自己做的饭不合我的胃口,命令萧以辰留下来,做完饭再回去。
有很多时候,我都不是很懂他。
这些事情,明明让佣人就可以做,他作为裘氏集团的创始人,一看就不是经常下厨的人,但我和他住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其实吃得最多的,就是他做的东西。
之前我生病的那时候,他将许芮接了过来,又一次许芮没忍住,在餐桌上故意嘲讽了一句:“没想到裘总还会做饭。”
他当时皱了皱眉,可又将目光投向了我,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认真的答了一句:“当年余正涛进门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妈不在家,饿了很久,后来就自己学会了。”
他说得太过认真,以至于说完以后,我和许芮都接不上话。
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听了他上半个故事,就更不知道说什么。
我心里漫无目的的想着,突然就觉得异常的烦躁,没忍住,点了根烟来抽。
——我是不怕抽烟影响我肚子里的孩子的,我巴不得他能够流掉。
我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碰烟了,自从蒋正南死后,我碰烟的次数就不是很多,但此时此刻,我怎么也忍不住,我依旧坐在窗台上,半曲着腿,一根烟夹在指尖,我抽的很凶。
烟进入我的肺腑,和我绞痛的心脏挤压在一起。
一支烟抽到尾部的时候,我忍不住想,我要快点找到突破口,让他伏法,这个事情越拖下去,就只会纠缠得越深。
我不能再拖了。
但在这之前,我得想办法,把许芮送走。
想到这里,我将烟掐灭了,可还没等我站起身,房间的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房间里尼古丁的味道都还没来得及消散,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声,就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裘钧扬。
他做了一顿饭,可身上不见丝毫油腥气,依旧俊美得如一根标杆一样。
他皱了皱眉,那双摄人的眸光朝着我看了过来。
从医院回来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就一直弥漫着一种一触即发的压迫气氛,我能感觉到他压抑着某种束手无策的暴躁,却又因为常年累月处在高位而磨砺出来的内敛而没有发泄出来。
我手指不由自主的微微紧缩起来。
我确确实实怕他。
我既恨他,可又深入骨髓的怕他。
我站在窗台边,紧绷着身体,不敢动,只是冷静的看着他。
我以为他会发怒,毕竟他已经隐忍了这么长时间,从医院回来的一路上,我都觉得他身上有种着暴雨来临前的风雨欲来。
但他没有动,过了半天,他胸口起伏的幅度才平缓下来,朝着我道:“过来。”
我没动。
他站在原地,无声的压迫着我。
我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从窗台上下来,去到他面前。
裘钧扬一手揽着我,和我一起到了餐桌旁,道:“我问过六六了,她说你这个时期吃带点酸味的东西口味会好点。”
我垂眼朝着桌面上看过去。
桌面上是砂锅粥堡的一锅白粥,不稠,清清淡淡,旁边配了几个凉拌小菜。
都放了点辣椒。
还堡了一蛊熬到发白的鱼汤。
他先给我盛了点鱼汤,放在我面前。
我肚子确实饿了,并没有拒绝。
绝食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措。
这顿饭我胃口确实好了不少,至少呕吐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吃完饭,他的电话响起来,脸色变了变,站起身去到窗边接了起来,身上的气压低沉得压抑着整个房间:“有事?”
“我没有什么好见的。”
“你告诉他,死了这条心。”
他说完,脸上已经冰冷得没有任何情绪。
房间里的温度也瞬间降低了起码十度。
我很好奇,到底是谁让他这么抵触。
但我没去问。
第二天,他将我带去了裘氏集团的总部大楼。
车子刚到大楼前,有人迎上来:“裘总,江总来了,在会议室等您。”
我猛地抬头朝着对方看过去,不知道她说的江总,到底是哪个江总。
裘钧扬却是眉头一拧,寒声的道:“谁准许你们放他进去的?”
那人脸色白了下来,支支吾吾的道:“江总他……”
裘钧扬本来气就不顺,这会儿气压简直沉到了底。
他带着我大步朝着电梯那边走,一路上脸色就没缓和过。
直到电梯到达高层,他出了电梯,还没往里走,就在走廊尽头看到了一个人,背对着我们这边,手指间夹着烟。
待看清那人的背影,我才狠狠松了一口气。
不是江钦离。
那人应该是听到了脚步声,转过头来朝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整个人一愣。
我却又猛地皱紧了眉头。
这个人我认识,是江钦离的父亲,江镇。
江氏集团的上一个掌舵人。
他来找裘钧扬?
他的目光接触到裘钧扬的那一刻,整个人有些慌乱,赶紧掐了指尖的烟。
“钧扬。”他叫了声。
声音里甚至有些故作的亲昵。
我拧了拧眉,江钦离恨不得弄死裘钧扬,我还以为是江家和裘钧扬有什么血海深仇。
毕竟他混到这一步,结过的仇家太多了。
但江镇的态度,却让我觉得奇怪了起来。
“我觉得你叫我裘总更加合适。”我还来不及细想,裘钧扬就开了口,他嘴角嗤笑一声,道:“不知道江总来我这里,是有什么事?”
“我……”江镇说道一半,猛地顿住,将目光投向了我,嘴巴顿时抿得紧紧的。
有些难堪。
“如果江总没事,那裘某就失陪了。”
“钧扬!”江镇一时之间有些慌乱起来,他道:“这些年你……”
“过得很好。”裘钧扬寡淡的笑了一声,那笑意凉得刺骨,却也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怕是你江总家的少爷也不如我混得有权优势。”
“裘烟她……”江镇好像并不想和他谈这些,转了话题,但转了以后,又有些难以启齿。
“她很好,有爱的人,有孩子,不劳烦江总挂心,倒是江总要好好教教自己的儿子,免得引火上身。”
我心里狠狠的跳了起来。
有一个模糊的猜想,在心里慢慢形成。
江钦离对裘钧扬的敌意。
江镇对裘钧扬的愧疚。
以及他问到过的裘烟。
裘钧扬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和裘烟总是在搬家,裘烟有一阵子,总是忍不住在哭。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是想躲着谁?
裘烟那么刚强的人,为什么会偷偷的哭?
我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
如果我没猜错,当年裘烟跟着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江氏集团上一个掌舵人,江钦离的父亲,江镇!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